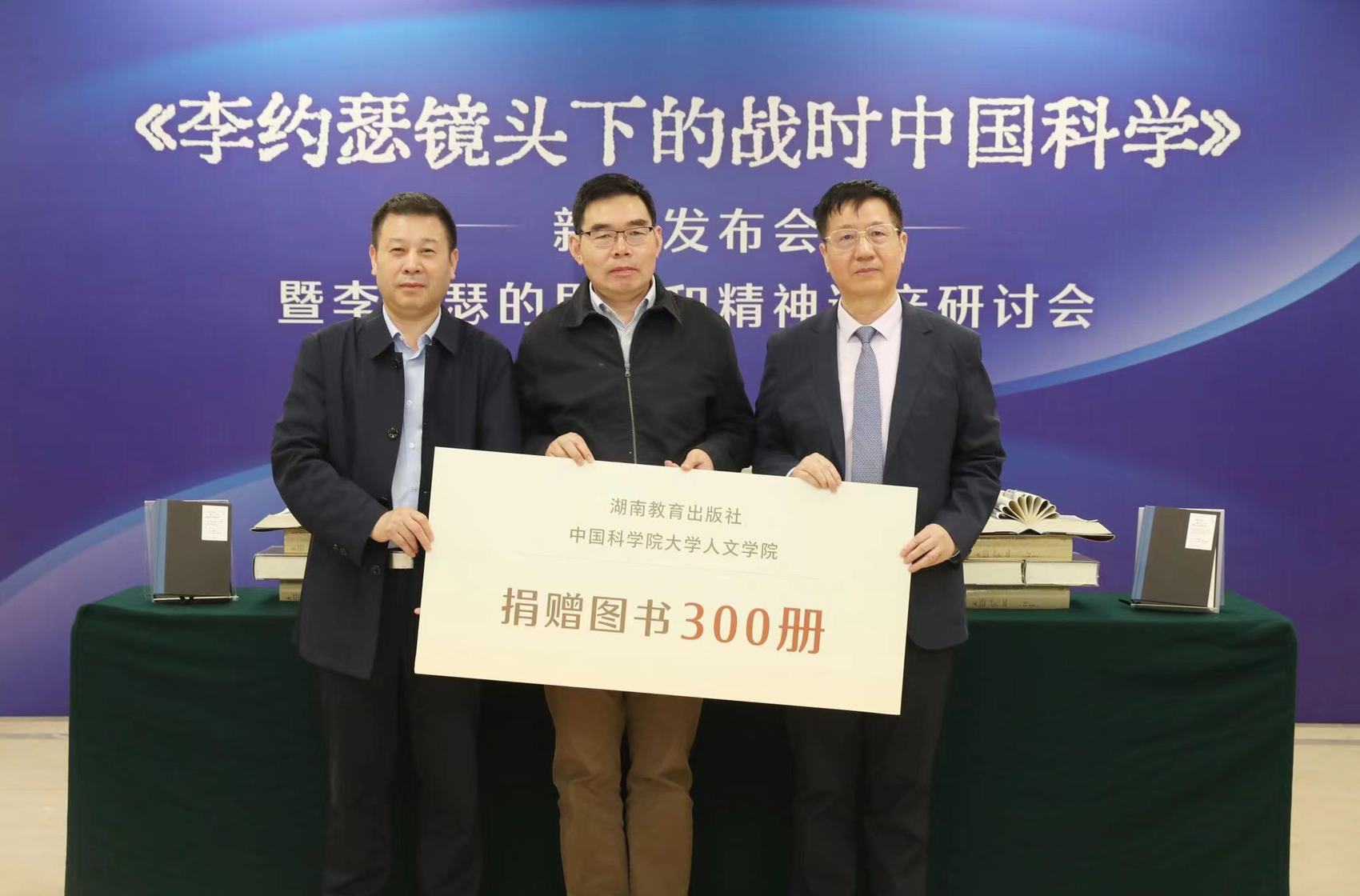特约记者|赵颖慧 张 琴 摄影|秦 楼
“行走的时候带上灵魂,腿脚所及之处灵魂也一应到场,让生命价值实现提升,实现生命与世界的同步重构”。
“只有你身体抵达过的地方,才是你的世界;只有你灵魂纠缠过的人事,才是你的历史”。
7月28日,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龚曙光散文集《满世界》首发,引发关注。韩少功、李修文、穆涛和刘大先等名家汇聚,共同探寻个人生命与世界文明、身体旅行与灵魂放飞的人生命题。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谈中,五位谈话者与百余名观众一道逆着时光之河往上游走,在思想的吉光片羽中追溯国人游历海外、考察世界的进程,面对世界变化与更迭,解读游走世界的全新意义。
与前人不同,作为新时代文化人的代表,龚曙光并不是急于印证业已发现的世界,而是以世界为镜,书写出不偏倚、不愤嫉、不卑亢的生命感悟。与其说,是他一个人将世界走遍,不如说,是他将世界摄入他自己的灵魂观照之下。
穆涛剖析,“在他的笔下,既有对异文明的精确判断,也有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反思,还有对各国文化的比较和思考,以及关于未来的洞见和建言”。“他的行走,是瞻望世界文明与文化的重要坐标,是高精度、高敏度、大口径、大焦段的世界观透镜”,韩少功如是作结。
“行走的时候带上灵魂,腿脚所及之处灵魂也一应到场,让生命价值实现提升,实现生命与世界的同步重构”,怀着深思与追问,《满世界》里的龚曙光如是领悟。而行走和观看中,同步实现了他的体悟与认知的合一,加速了他作为个体与世界的重构。
巨大的平静中,他向洋看世界,将自己融入了那些器物、那片山水、那段历史人文。
龚曙光:一场个人生命的“田野考察”
龚曙光:我一直认为旅行对于一个人,是一种特别好的生命放松过程。我们的生命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格式固化,旅行是最自主的一种自我解放方式。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对两种基本的关系,其实也是两个难题:一是个体和群体,二是身体和灵魂;而作为一个文化人还要面临两种关系:一是今人和古人,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旅行恰恰会把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两组关系扭结起来。
现代社会,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我们的灵魂都被各种结论所禁锢,读的书越多,所受到的禁锢也越多,因为我们总是在接受别人给定的结论,而很少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走出去旅行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一场个人生命的“田野考察”。
我的“田野考察”,是基于我对生命的企盼或隐忧。我之所以把今天的对谈主题定为“生命与世界的同步重构”,是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办法不面对世界,因为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既然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的世界,我为什么不可以迎上去呢?为什么一定要躲避呢?为什么一定要以一种先验的拒斥态度去对待,而不是以一个裸体的生命去迎接它,去感受它的优长和劣短,感受它的柔软和坚硬呢?所以,实际上,我的旅行是我有意识地朝着世界的来路逆行。
满世界的行走的确改变了我。比如我对希腊的认知,大家都知道荷马史诗、都知道古希腊神话、都知道希腊是以美为宗教的文化源头。但只有我到了爱琴海边,才明白为什么是希腊把美奉为神祇。看着爱琴海湛蓝的海水和海岸边白色的房子,我才明白为什么希腊人的美那么简洁、那么单纯,而又极致到你没办法超越。这样的感悟,是没有办法在任何一本书中知道的,只有在爱琴海边,你才可能认识到人类自圣的极致是美,美是不可超越的。
有一个朋友作了一个统计,《满世界》中三分之一强是关于自然的描写,三分之二弱是关于历史、文化、文明的议论。在后一部分中,大概有一半的文字是对灵魂的表述。这种灵魂在自然山水中的自由旅行,实际上是生命对世界的一种求证和发现,所以我说它是生命的“田野调查”。
这些自然风物的描写,当然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等前辈的风物描写不同。我所看到的布拉格、克罗姆洛夫甚至同和我同行的人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确实把灵魂完全融入了那些器物、那片山水、那段历史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不要在意这本书究竟提供了怎样的结论。我对很多问题确实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如“文艺复兴的真正武器,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人手中的金币。艺术,不过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战利品”。我认为这个结论只属于我,属不属于你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把旅行当作有限生命中,可以自主实现的改变生命的契机,旅行会让我们的生命获得意外的价值。
韩少功:深者见其深、活者见其活、实者见其实
韩少功:五四以来,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上百年。但直到今天,我们如此大规模的与世界迎头相撞,有强度的冲突也有深度的融汇,是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精神都是很大的挑战。现在需要把思想解放出来,重新观世界,重构我们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中国人其实特别内向,不大善于往外看。大都定居在“张家村”“李家庄”的农耕民族,比较畏惧也不太擅长和外界打交道。比如,唐人街就是中国人的一大景观,说是到了国外,但他的心态和灵魂还在中国的“张家村”“李家庄”。我碰到很多海外的老华侨,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说几句外语。有个入美籍20年的老朋友,聊起美国时,都是下意识地说“他们美国人怎么样”。我说,你都入籍20多年了,怎么还是“他们他们”的?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满世界》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出版,可以带动和引领更多人来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中南传媒的钟叔河老先生,把100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等精英走出国门看世界的观感整理记录下来。但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自我定位,真正把自己既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一个世界人,如何处理与外界的关系,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满世界》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建设性的添砖加瓦。
从现在很多游记可以看到,很多人看世界大多时候少见多怪、大惊小怪。有一次,一个作家代表团到了俄国,看到一些油画特别惊讶地说:“你看人家的皇帝多么有文化,我们的皇帝多么野蛮。”我说:“宋徽宗的画你见过么?唐玄宗写的字你看过吗?我们汉武帝、李后主写的诗词你知道吗?”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正要把整个世界看懂,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我特别欣赏这本书,总结了三点:深者见其深,活者见其活,实者见其实,这是这本书最可贵的特征。
曙光在出版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现在出版了两本散文集,被称作“文学回归”,好像此前的经历耽误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干点实务对他理解和观看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帮助。他在书中提到好莱坞的电影、意大利的时装、日本的动漫等等,我一看就会心地笑了。就因为他干了这么多年的出版和文化产业,他能看出门道,一般旅者看不出来。所以必须在实际中摸爬滚打有了职业敏感以后,你看这些东西才会真正有所收获。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去道听途说,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这个世界,达不到这样的深度。
龚曙光:少功提到的这一点,的确如此。不大会有一个游记写作者去写经济,我的这本书估计有10%的篇幅是涉及到经济的,有的涉及到较深的经济或者金融运行逻辑的思考。实际上这本书涉及的学科领域约有几十个,仅文化产业,就有电影、动漫、游戏及传统手工艺等,要把这么多行当的门道弄明白,还要得出自己的一些思考,靠临时读书恶补是不行的,这来自几十年的观察和沉淀,有真正的生命体悟在。
我也觉得这些东西,虽然从传统文学来讲可能有些越界,但我总是力图通过用灵魂对这些经济形态的领悟进入审美范畴。这种写法文学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贾谊的很多文章都是奏疏,有关于粮食储备、经济运行的,我们不也读到了文辞之美?不也读到了浩荡的灵气?我认为一个文学家只要把灵魂摆进去,不管你面对的是历史还是经济,是艺术还是器物,面对的是山川还是流水,我认为都会具有审美性、都可以以美的形式来传达。
李修文:保持对生活百感交集的能力
李修文:龚老师的写作,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叫作“永远主动在生活,然后被动地等待写作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保持着对生活百感交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从《日子疯长》开始一直延续到《满世界》,我觉得非常鲜明、突出,弥足珍贵。
第一,在态度上,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平静”。他没有《北京人在纽约》式的大惊小怪,没有那种国境线打在身上之后所产生的挣扎。他其实既代表作者也代表今天的中国人,当我们真正开始外观世界、内观自身传统,面对这个世界的到来和复杂性时,终于活成了一个平静的人。
第二,这本书的文气非常充沛。这一点早在《日子疯长》时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今天的主题“生命与世界的同步重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文章和旅行的“知行合一”,就是人和世界不断融入彼此。这本书展现出来的生命姿态,其实也在回应着我们中国的传统,回应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目即成实”的传统,意思很简单: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李白是这样,杜甫也是这样。朱熹讲文人之“图”,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充实。“充”就是不断填充自己,扩大自己和世界边界的突破和互相的蔓延;“实”,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及物,去和身边遭逢发生最真实的联系。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需要多少场平静的审视,才能获得最终写作上的平静?所以这是对我自身写作的很大启发。
我非常羡慕龚老师这样的创作力。我认为龚老师的创作现在仅仅是一个起步,我读过一首诗,大意是说“五十岁以后重新活回了少年”,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所展开的准备。我们看到《日子疯长》,他对于乡土切实的描述、凝望,只有生活在江汉平原一带,生活在湖南水乡才能领略到那种真实的感受。再到今天的《满世界》,这种巨大的平静,这种针对常识出发并不为常识大惊小怪、撕心裂肺的气象和境界,其实可能仅仅是他未来更宏大作品的一个起点。
龚曙光:在跟世界逆向的行走中,有些东西相遇之后相处很和谐,有的东西会发生对撞。因为我这一辈人所受到的中国文化教育虽然有限,却十分强悍,它必然会和我们在行走中所邂逅的这些人类文明的样式、人类文化的范本、人类生存的模式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甚至会强烈到怀疑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一切。但对撞之后的平静和宽容,使今天的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愤青,不可能是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
所以,在这十几万字中,唯一带点“愤青”印迹的只有一处。在俄罗斯一章,当我写到“娘炮”的时候多多少少提高了一点嗓门,其他地方尽管内在的冲突可能激烈,但我的表述是平和的。当我在世界来路的逆行中,相遇任何一种文明,哪怕是与我们有巨大反差的生存方式或者文明范式时,我也不会去排斥它。因为满世界的行走,给我的精神带来一种更宽广、更平和、更超拔的气象。每一次旅行,都加深了或者加厚了我跟世界的生命重构。
穆涛:打量世界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心态
穆涛:《满世界》这本书读的时候很舒服,有意思、有意味、有意趣,对我有三点启发:
第一点,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这是一个写外国的游记,用什么样的眼光去打量去观看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心态。我们新文学100年出头,国门打开后写过不少国外的游记,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都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在写作?有觉得国外什么都好的,想学习先进经验的;也有自卑自艾、百感交集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很落后,我们仰望、惊艳,觉得怎么世界这么好、科技这么好?这种心态挺不舒服。但这本书就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把看到的东西慢慢讲给你听,他是平视的、交流的,他写布拉格,写东京,写巴黎,跟他去农家乐、去看乡村没有区别,这种心态很重要。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游记写得好的很少,但这本我真觉得好。现在的游记很多都是依时之见、依人之见,如果作者读书少、阅历少、心态又有问题,这是很可怕的,而且依时之见问题比较大,受各种社会影响、干扰,会出很多问题。我举作家杨朔先生写的《泰山极顶》为例子,杨先生写大集体、合作化,写到看到泰山一户人家院子里有只鸡,雨后走的那个脚印是“个”字,他说,鸡都觉得太个体了不好。我认为鸡不应该有这样的糟糕境界,这是对鸡的严重不尊重。依时之见,出现的问题是很大的,而且这篇文章入选了大学教材、中学教材,这是要引起警惕的。
读游记要结合历史读,孤立地读游记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游记丢掉了一个大的传统:就是《徐霞客游记》《山海经》《史记•河渠书》式的传统,下扎实功夫,写出个人认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写,用发现的眼光去有所发现,而不仅仅是“仁者见山,智者见水”一类陈词。本书写作的路数,下功夫的路数,每到一处的路数,都是写自己的体悟、认知,而且不拘于文学抒怀,单纯抒情的不多,杂糅了记事、叙事等多重方式,这种写法和态度我觉得挺好。
第三点,我是编辑,我觉得好读的书都有一种文体感,如今每年创作的散文那么多,有文体感的作家不是很多。秋雨先生写得有文体感,而这本书也是有文体感的。文内章节都是用罗马数字标下来的,读起来浑然一体。而且好玩的是每一篇文章都链接了知识点,既作为强调又作为补充,这样的认真,就是对自己写作的尊重。同时又不让某一知识点所占的篇幅失衡,保证了行文的简洁、结构的均衡和文气的贯通。如此开阔的视野、驳杂的内容、随行走而成的结构,却能形成鲜明的文体感,很难得。
刘大先:生命与世界同步的媒介就是旅行
刘大先:读完这本书我很惊讶,龚老师是一个实业家,但没想到他是一个文气特别充沛的人。我认为生命与世界同步的媒介就是旅行,旅行涉及到两方面:一是自我的成长,一个是关于他人的认知。
人类社会几乎绝大部分部落都有成长仪式。青少年到青春期要外出游历,在游历中,他看到千山暮雪,看到万里残云,看到日月盈亏,看到万物的此消彼长。他参与了实践,让个体得到了成长,灵魂得到洗礼,这是自我的成长,是旅行的第一方面。
第二是关于他人的认知。旅行会涉及到你跟异文化的关系,你怎么走出自我狭隘、封闭的文化圈,走到一个不同的文化中去?是封闭自己还是敞开心扉接受它?是产生一个碰撞,遭遇一个文化震惊,还是进行文化接纳?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命题:自由与秩序的命题。旅行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拔”出来,是一个“出轨”的行为,秩序的破坏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个过程就会涉及到少功老师刚才讲的“观世界”和“世界观”。
《满世界》这本书写的14个国家基本分布在欧洲,这非常有意思,这是曙光老师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我们从空间的书写上基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历史的发展。从19世纪中叶开始算,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是在收缩大转型的状态。
先秦时代,我们是“天下为家”,是天子居于中间,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平推、扩展的宇宙图式,这使我们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是到19世纪中叶之后,我们赫然发现被强行拉入到现代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被欧洲定义的世界。
从14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海外殖民,这实际上是欧洲把自己的地方性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谓的“东亚”不得不被纳入到这个叙述模式中来,所以梁启超说,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我们派各种使团出去,日本也派使节团到世界学习。我们不停地学,学君主立宪,学法国大革命,学暴力革命,然后学俄国。整个150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欧洲扩展开来的世界观念。但这个观念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打破。在鲁迅时代,他就关注到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翻译。
到了新世纪,我们综合国力增强,不仅文化精英能走出世界,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全民旅游,这时我们对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任何一个工作都要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这样才会锚定你在这个世界的位置。龚老师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不是一本普通游记,他在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观。《满世界》里面有好几篇我印象非常深,比如他用“山口”来概括瑞士,他对韩国孤岛的个人化认知,对我特别有启发。这几十年来,散文创作好的作品屈指可数,我相信龚老师的《满世界》,是散文在新世纪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