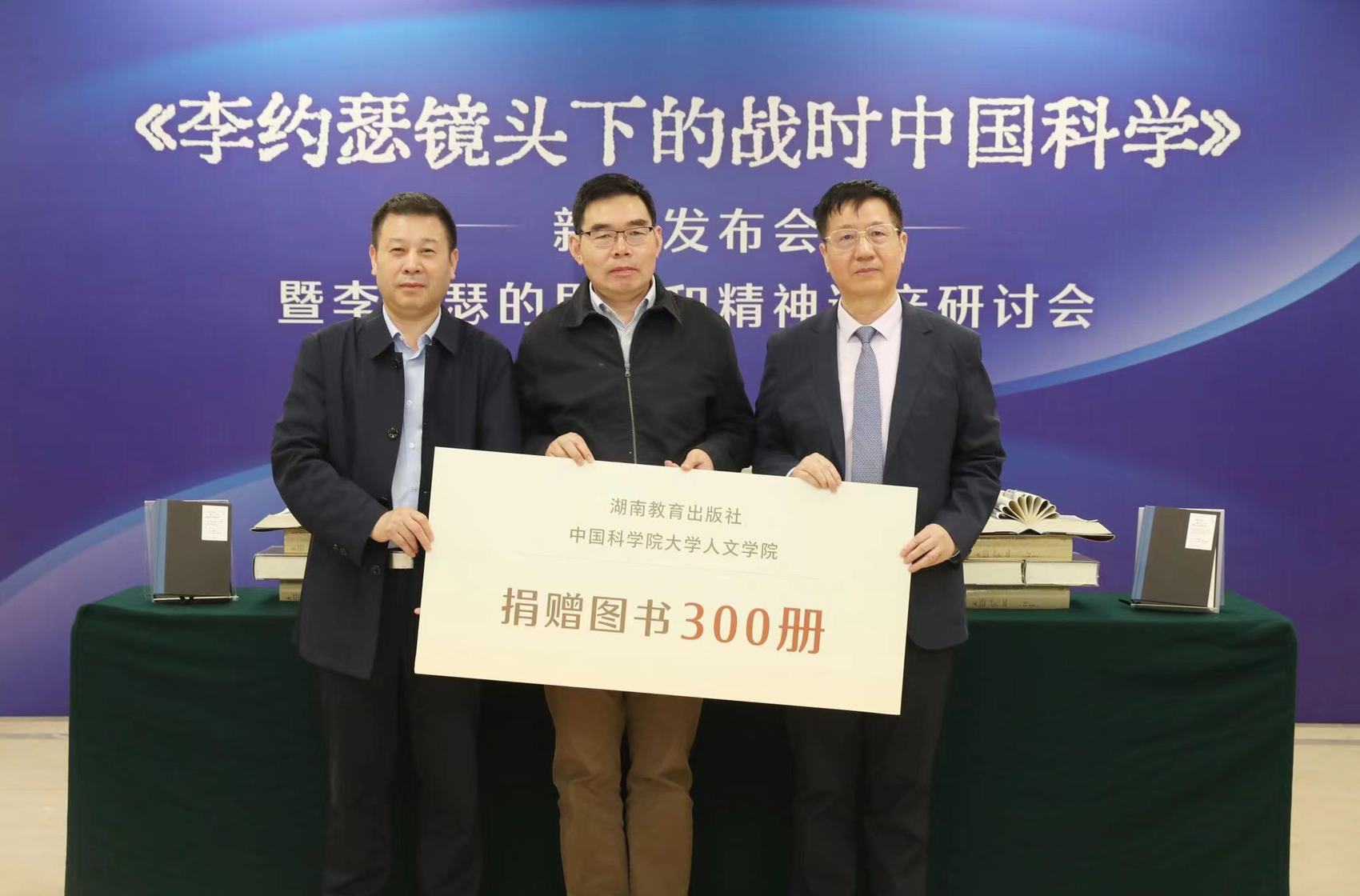我撰写和出版《阅读社会学》只是“一家之言”,作一次初步探索和尝试,为这一专门研究开一个头,拓展一个认识的视角,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黄晓新
一
我从小就喜爱书籍和阅读,至今还最爱逛书店和图书馆,一扎进去很久、沉缅于乱翻书不愿出来。记得在农村读小学时,有次我随大人到离家最近的镇子,第一次见到一家小图书馆很是兴奋。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一个小的阅览室,空荡荡的室内摆着几排旧桌椅,靠墙有一书架,上面横七竖八码放着些书报杂志。我废寝忘食地在里面翻看了一整天,小小少年对外界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心想,世界上还有这等好事,不要钱,还能安安静静读各种书,以后可常去,这应该是比天堂更美妙的生活……
然而随之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我那个小镇,打碎了我的阅读梦:年轻时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当军医的父亲,因为被划为“右派”回地方行医,而又被打成所谓“反动医学权威”,被抄家游斗,最后“身陷囹圄”,我家也因此“从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顿”。在那个出版和文化荒芜的年代,我只能在随学校开荒、种田、挖鱼池、砍柴等走“五七”道路、搞劳动的空当,从地下和垃圾堆的废纸篓里捡些散页和纸片来读,以此排遣自己内心的烦恼、孤独和苦闷,也曾为了让母亲买一本在其他小朋友手里见过的《红灯记》剧本不可得而独自哭泣……

好不容易盼到“文革”结束,那时我正在家乡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中。不久邓小平同志复出,高考恢复,群情振奋,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也随之投入到高考的洪流中。记得在填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把“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作为第一志愿,一是听人说学文史哲容易“犯错误”,学这个应用文科相对比较“保险”;二是好奇“图书馆”本身还是一门学问,毕业以后从事图书馆工作可以“坐拥书城”,圆“不愁书读”的梦想。天公作美,我于1979年9月正式踏入武大的校门,从此决定我一生与图书、阅读的缘分。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前身是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创办的文华公书林(图书馆)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武大),是解放初国内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比肩的仅有的两所有此专业的大学之一。在武大,我既学图书分类、编目,也学文献学、情报学、目录学、版本学、工具书,也学读者工作……毕业后,曾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年。1985年7月,我自知当大学老师知识储备不足,又考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关注读者和阅读。这时武大的“图书馆学系”已升级为“图书情报学院”,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发行学等四个专业系科。我的导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原副系主任孙冰炎教授成为刚成立的图书发行学专业的创始人,这使我在进行读者和阅读研究时有了另外的视角。
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出版发行学以及教育学来说,读者都是其服务和研究对象,读者是图书文献的接受主体,阅读行为是其本质特征,但在不同的图书文献工作部门却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对学校,读者是受教育者;对于出版者和书店,读者是购买消费者;对于图书馆,读者是图书文献的利用者……这些部门都要了解、研究读者和阅读,但视角不一、方法有异,囿于各自工作范围,不可避免有相当的“门户之见”。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学习中认识到,语言文字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阅读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社会活动,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获取知识信息的基本途径和手段。个人的社会化如学习知识、融入群体、摆脱孤寂等靠阅读,人类社会的“自组织”靠阅读,人类文明的传播、传承靠阅读……人类文明越发达,阅读越昌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越爱阅读,这个国家、社会就越文明、越发达,越有创新活力。一部人类进化史,正是一部阅读的升华史。世界上的阅读大国都是文明创新、富有活力的强国,无论是“小小超级大国”的以色列,还是欧洲的“带头大哥”德国,无不如此。
阅读是书报刊等文本(包括数字文本)的消费过程,更是这些文本传播社会功能的实现过程。一个人阅读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他的社会地位高低和他对社会的贡献。一个国家国民阅读力的大小和阅读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力。无论是图书馆、出版社,还是书店,读者和阅读都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和归宿。
15世纪谷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引发欧洲“阅读革命”,阅读方式从集体听传教士解读逐步变革到个体自由默读,进而改变世界,促进欧洲思想解放、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16〜19世纪文化教育的勃兴催生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教育和阅读的普及培养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工人,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上世纪初以来,阅读已成为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图书馆学、出版发行学共同研究的对象。1956年,国际上还专门成立研究组织——国际阅读协会(IR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5年在维也纳成立国际儿童文学和阅读问题研究所,1972年,明确提出“全民读书”的理念。1997年更是发起全球“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倡议。197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阅读协会会议上,宣称“一切人享有阅读权利”,并且提出“迈向阅读的新境界”的口号。此外,国际出版商协会(IP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等国际组织都大力倡导和推广全民阅读。
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断流,主要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崇尚阅读、传承丰富的典籍。千百年来,我国民间流传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千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的格言,流传着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等的阅读故事,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生活就是“公卿白屋”“渔樵耕读”。近代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现代新闻出版业和公共图书馆的兴起,阅读活动逐步走出传统的私塾、私刻坊、私家藏书楼等空间而公益化、大众化、社会化。
然而,翻遍国内外阅读研究论著,主要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领域,从社会学角度来认识和研究阅读的文论很少,成体系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因为社会学还年轻,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阅读现象的认识还存在局限。
二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阅读的社会调查也刚刚开始。我感到我们有必要走出学校、图书馆、书店、出版社,摆脱“屋”的羁绊,跳出对阅读行为的个人、微观、心理等的认识局限,从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来考察、研究阅读活动和阅读现象,于是我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1987年10月)发表了《阅读社会学刍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定为《关于阅读现象的社会学思考》,该论文从“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与社会的互动”“阅读需要及其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等方面初步论述了阅读与社会。在此基础上,我还在1988〜1991年的《图书情报知识》《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上整理发表几篇习作。但总体感觉意犹未尽,因为阅读与社会是一篇大文章,不是短短几篇小文就能够论述清楚,更何况阅读和社会及其互动都还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中。
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北京从事新闻出版管理,先后在机关做过发行、市场、音像复制等监管工作,没有离开出版与阅读,同时也始终关注社会阅读活动的开展。
随着移动数字新技术兴起,传统纸质阅读方式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还有我国应试教育的弊病及对学生阅读力的影响,使阅读成为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加强阅读社会学的研究。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其宗旨在于让阅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2006年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12部门部署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开始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7次提到“全民阅读”,一次比一次力度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社会阅读工作,并身体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鼓励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在接受国外媒体专访时表示:“阅读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还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的活力,让人得到智慧的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谈到:“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并表示这也是连续几年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原因。
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已经开展十多年,全社会“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各类读物丰富选择,阅读的基础设施(如各类书店、书屋、图书馆等)更加完善,阅读组织层出不穷,阅读活动推广的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阅读立法和组织协调机构有力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已取得相当进展和成绩。我感到总结全民阅读的实践认识成果,开展阅读社会学研究的条件、时机越来越成熟。
为了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见识,2011年8月—2014年8月,我志愿报名、组织委派挂职援疆三年。回京后,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任职,体现了组织的信任和重托,也符合我干点具体实事的初衷和理念。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为我国唯一的新闻出版专业智库。该院从1999年开始,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委托,至今连续开展了16次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2007年,该项调查获得中央财政资金,从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以了解国民阅读与购买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变化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受到读者、出版者和教学、科研、管理部门的普遍肯定和好评,调查所得资料被广泛引用。该院还成立有“国民阅读研究和促进中心”,不定期出版“中国阅读蓝皮书”。为交流全民阅读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该院还办有《新阅读》杂志。
在这种情况下,即全民阅读实践的要求加强阅读的社会学研究,丰富的阅读的社会调研材料为阅读社会学研究打下基础,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也为深入开展研究提供借鉴,而我置身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更是为我的研究提供养分,使我如鱼得水,有机会捡起30多年前的旧课题,着手基于新的全民阅读的丰富实践开展研究。
坚持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紧密结合社会阅读的实际来规划和布局谋篇,我列出10个方面的内容,也是阅读社会学的10个课题,期待这形成“阅读社会学”的基本架构,也是一个封闭的认识、管理社会阅读活动的结构。除阅读社会学概论外,主要有阅读的社会过程、阅读的社会效能、阅读的社会心理、阅读的社会结构、阅读的社会互动、阅读的社会产业、阅读的社会组织、阅读的社会保障、阅读的社会控制、阅读的社会调查监测评估等。
按照上述思路,2016年我主持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课题《阅读社会学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书稿。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刘建华、卢剑锋、屈明颖、田菲、徐升国等同志对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三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热情鼓励、关心和支持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审阅了书稿并欣然亲笔为该书作序。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一直热心关注、促成我们的研究,并对该书稿的撰写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时任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辛广伟总编辑和张文勇编审、赵新博士等的支持帮助下,《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一书有幸列入“中国学派”丛书系列进一步修改完善,于2019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
2019年7月13日,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联合在京举办(《新阅读》杂志社承办)了《阅读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一书的出版研讨会。来自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研讨会,他们对《阅读社会学》给予肯定与好评,认为该书是首次对近十多年来中国全民阅读丰富实践的科学的系统理论总结,是指导当下及将来全民阅读工作的有力思想理论武器,能够在促进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工程中发挥比较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到会祝贺该书出版,认为该书视野宏阔、学术厚重、系统周全、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融通中外,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日益重视全民阅读的今天,这本书的出版对制定全民阅读政策和措施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也将对各地的阅读推广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于殿利发言认为,作为国内第一本总结升华全民阅读的理论著作,该书抓住了阅读的本质,既有开山奠基性的学术价值,同时又针对中国社会阅读状况设置议题,具有促进社会阅读推广的现实意义。
老领导柳斌杰同志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其“逻辑严密,结构合理,使用方法得当,论述系统周全。从理论架构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看,可以称得上阅读社会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中国教育学会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朱永新强调:“《阅读社会学》从理论上为全民阅读提供方向指引、学术支持和方法选择。”
韬奋基金理事长聂震宁认为:“《阅读社会学》是一朵盛开在我国当代全民阅读生动实践之上的理论之花,全书立意新颖而鲜活,内容切实而生动,是阅读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专家学者对该书的肯定和媒体的报道是对作者的鼓励,也是鞭策。我深知,由于自身学养和知识的不足,该书错漏一定不少。我撰写和出版这一论著只是“一家之言”,作一次初步探索和尝试,为这一专门研究开一个头,拓展一个认识的视角,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文至此,欣闻“全民阅读”又一次被写入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体现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这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战略工程的高度重视。相信随着国内国际全民阅读实践的深入,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理论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