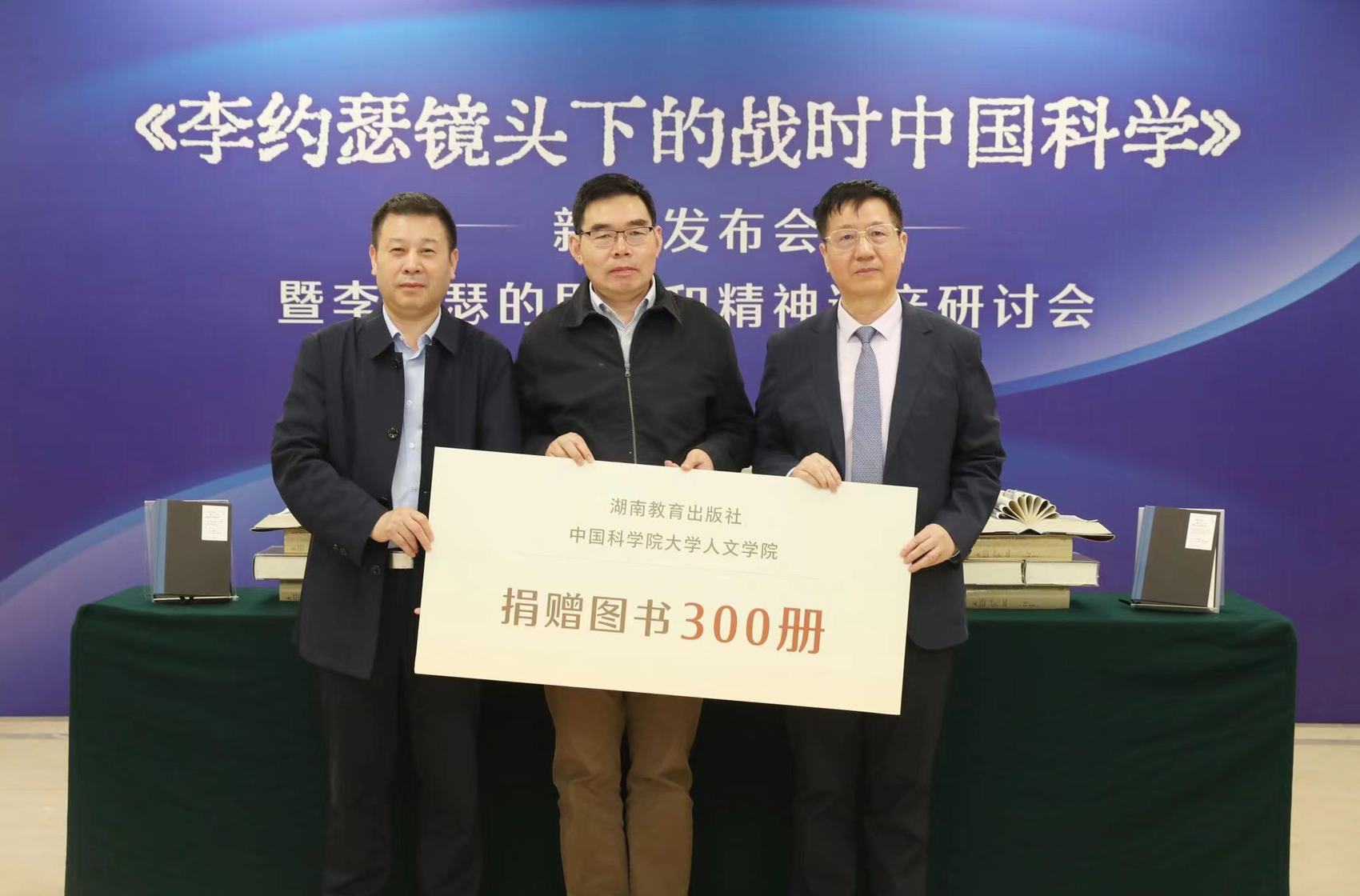在这个无物不可见、无地不可达的时代,我们从不缺乏有关乡村儿童的讯息。然而讯息的“轰鸣”不等于认知的深度。事实上,在包括乡村讯息在内的数字化洪流中,毫无节制的“呆看”成为一种“遍览”式的呈现。正如老子很早就提出的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阅尽无数讯息和数据,堆积出了高度同质化、碎片化的乡村印象。某种程度上,“乡村”叙事在“美丽新农村”和“扶贫攻坚”之间摇荡,在乌托邦漫谈和“苦难叙事”的张力之间构成它的姿态。
这时候,尤其需要“一束光”照耀这片被“狂看”的世界,需要对城乡的“差异”而非“差距”进行一场靠近和对话。这是舒波辉新作《逐光的孩子》所开掘的文学意义:在多年对底层儿童、支教青年的访谈过程中,在长期与弱势儿童群体接触、对话中,舒波辉以“行动者”的身份,融汇着所遇、所思的一切,选择、编织特定的故事,投以光束,从中提取清晰、生动的景象。《逐光的孩子》不是对贫困山村、失学儿童、乡村教师、支教青年等元素的简单堆积与再现;而是对贫困山村儿童生存境遇与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困境、支教青年的精神与情感救赎等系列问题的深度挖掘中,释放出“逐光的孩子”背后整体生活世界和文化精神之网。客观之眼、悲悯之心、诗意之笔,挥就了《逐光的孩子》那束穿透刻板印象、固定模式的光芒。
故事从“我”这名即将读研,因为女朋友(严玲)殉难在支教的山村,特地前来进行“情感疗伤”的大学生的视角展开的。故事起头“我”一心想去女朋友殉难的香溪小学,却被安排到更困难的蓝溪小学;“我”并没有因此反对和抵触,而是顺其自然地来到了神农架深处的小学校。在哪里支教也许并不重要,“我”最困惑、最想解开的答案是女朋友为什么要去支教。带着这份求解的困惑,“我”最初的支教生活,是“他者”般的客观冷静。但是随着“我”对郑天齐等山村儿童认识的加深,对齐老师装着义肢坚守学校的感佩,“我”那客观、透明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烈、激扬。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主动去寻找走失的郑天齐,主动通过所在高校团委和宣传的力量帮助蓝溪小学拉赞助、修马路⋯⋯可以说支教不止是“送”教下乡,还激活了支教青年本人更宽广的情怀和力量。
在张弛有序、疏密有致的故事节奏里,舒波辉充分调动了他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对诗性语言的执迷,使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叙事者的身份,来安放他对生命光影的诗意追寻。从城里来的“我”走进山村时,“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很多倍。除了一路相随的阵阵松涛,飞鸟踏枝的响动之外,很多幽静的虫声和草叶在风中歌唱的声音,也都从寂静中升浮起来”。严玲对“我”说过,“他们不叫贫困生,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也是我们自己”。在亲历支教生活后,“我”更加理解了逝去女友的选择,更洞悉了爱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他用女友留下的教学日志中一首诗(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的一首童诗)开启了一场感知生命和自然的语文课,“煦暖的春日从峡谷里缓缓升起,日渐丰润的蓝溪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金子般的波光。阳光下的孩子们像是风中交头接耳的麦穗,也像是田野里相互触碰的花朵”。在如此动人的教育下,郑天齐、白花蕊、陈高翔们用不同视角和表达写成的作文,相映成趣;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智障”少年覃廷雍的作文:“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让时间走慢,在大家都快乐的时候。我希望长大后,我有办法管住时间”⋯⋯在这些如梦如幻、亦智亦愚的诗性表达中,可以瞩目到儿童那纤弱而柔韧、斑驳而炽热的童心穿透了生活的沉重,像一道道充满希望的光芒,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本文作者为儿童文学评论家)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杂志2020.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