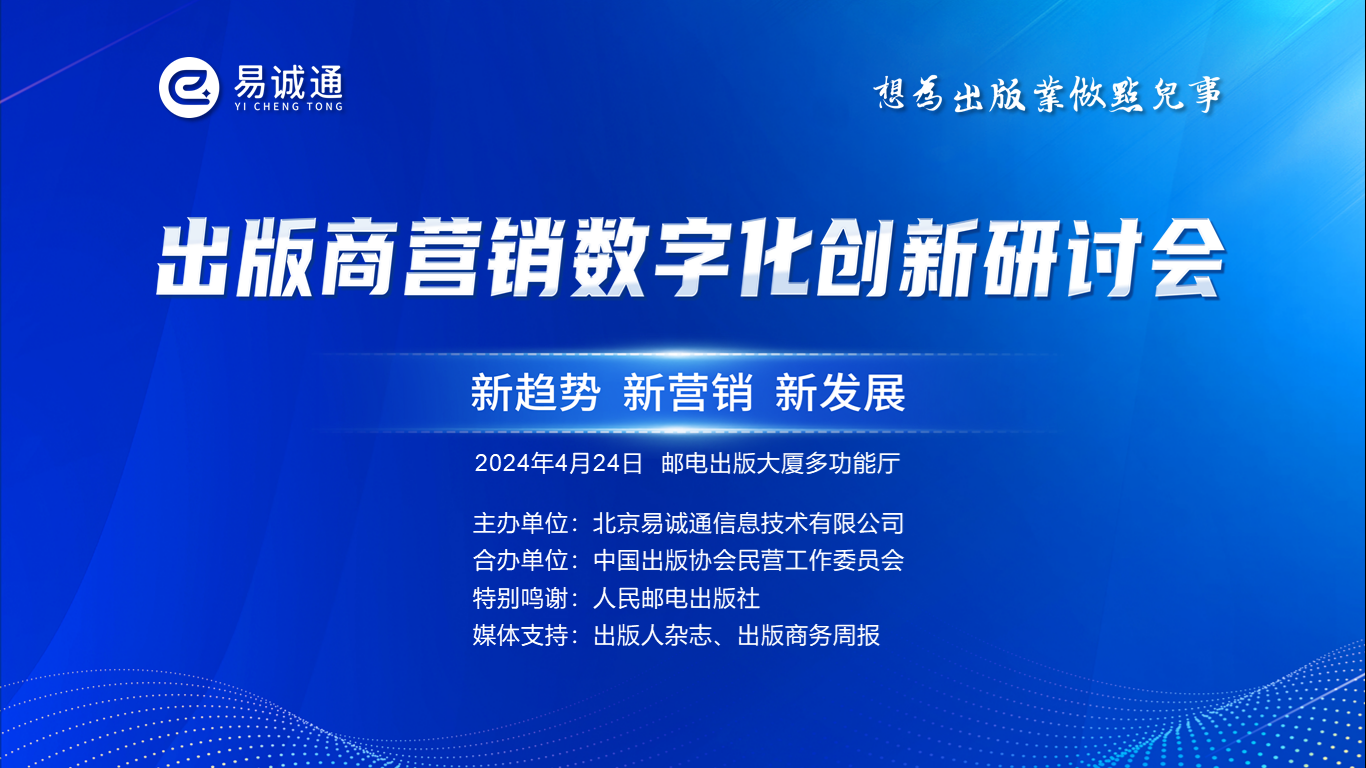记者|黄 璜
一家专注于原创文学的图书公司是否能在当下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2016年成立的乐府文化出发于原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涂涂与朋友们在出版市场的一次实验性探索。
在行业众声喧哗的背景里,过去五年,乐府文化推出了超过80种图书,其中不乏《秋园》《中国故事》这样叫好声一片的作品。
乐府文化以其理想主义的出版视角以及对原创文学的独到挖掘收获了众多同行的尊重。然而,它并不具备范本价值。涂涂曾在一篇手记中将乐府文化描述为“一家出书最慢的出版公司”,由媒体人转型而来的涂涂自己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出版人——公司驻地北京却长期居住在大理的他从行动效率上就有别于传统的创业者。涂涂很任性,这种任性既体现在他对边缘原创声音的选取,也体现在这样一家20人体量的公司如今正在推进超过150个产品选题的出版。
在出版市场,任何一家成立时间超过5年的公司都不会像乐府文化一样,在产品上追求多样性、可能性的同时还收获了行业的口碑与赞誉,却又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上保持着非常原始粗糙的状态。而后者,正是这家公司在当下遭遇瓶颈的核心原因之一。
从外部去看,乐府文化身上聚焦了很多悬念,文本的价值在市场如何获得更好地兑现?一家专注于原创文学的图书公司是否能在当下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我更为关注的是,创立五年之后,乐府文化如何跨越公司生死存亡的那条线,维持良性的运转,以及涂涂如何在不丢失理想特质的前提下构建乐府文化作为一家出版公司的系统能力,提升运转效率。换句话说,涂涂与乐府文化需要去直面理想主义之外的取舍与妥协。
不过,在和涂涂的直接对话中,很多问题尚未有答案。
乐府文化最初并不是一个商业公司
《出版人》: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创立乐府文化这个公司的?
涂涂:几年前面临着媒体的衰落,我想要去调整,那就需要去寻找另外一件事。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做出版。出版行业和我关联性最强,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在一个传统媒体呆了许多年,看了许多书之后,我觉得出版还有空间,依然有些书没有人做、有尝试的可能。我所理解的出版,是一直在寻找可能性的行业,它有确定性的头部,但是很多的确定性的头部,最初也是从可能性长出来的。既然有这个可能性,我就想试一下。
开始的时候,乐府文化还有类似乌托邦的梦幻想象,我们有8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完全平权的公司,大家投入都不大,由我来具体操盘,但是实际上公司是大家的。
这8个人有做过创业公司总编辑的,有跟我一样做媒体的,有做中小学教育的,也有作家。我们一起进来做这件事,完成初期的选题积累,它的想象空间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但实际操作下来不是这样,因为做书这件事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副业,只对我是主业。我慢慢发现,虽然大家热情很高,但只有热情并没什么用,在操作层面困难重重——乐府成立之后,第一年只出了一本书,第二年也只出了一本书。
《出版人》:这种平权式的结构,显然会对管理产生极大的挑战,后面是如何调整的?
涂涂:乐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商业公司,它起初带有很强的同人性质,但是它又有在商业层面的想象,这样的组织结构在当时我们觉得能做成,然而事实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在挑战人性。最后只能一个个退——我把原始股东的钱都退给他们,每个人保留一小份股份,算是留一个念想。
这个过程会有痛苦。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有梦想,而且有非常巨大的情感投入。必须实话实说的是,如果没有开始的这个结构,我不一定会做这件事。开始创业其实是挺难往外迈的,所以有朋友们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当你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在管理上很多时候也是挑战人性的,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员工坐班。
之前我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我都会跟对方说,乐府文化有很多梦幻、理想的东西,我也希望能够一直照顾到乐府文化的梦幻和理想,但同时它有非常明显的弱点,就是它的系统非常差。乐府文化现在有11个编辑,但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和11个不同的编辑部一对一地在做产品。因为编辑部本身不进行协同,所以有的新编辑不知道整个流程怎么做,这对编辑来说挑战性极强,有的就会在这个过程里失败,熬过来了就很好,出品率很高。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公司五年了,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好的系统支持。这里面有我自己管理上的弱点,因为我很懒。
我现在会想,也许我们还是应该有最基本的制度,让它回到商业中去做一个公司。但与此同时,我还是觉得,正因为乐府文化没有那些东西,所以在获得选题和选题执行层面有非常活跃的部分,因为我们确实给了编辑很大的空间和时间。作为一个出版公司,在现在的出版市场上,我们立足的基础点其实就是创造性。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出版人》:大家因为梦幻和理想聚集在一起,也会因此做出很精彩的产品,但是从外部来看,我们认为乐府文化到了需要去提升公司效率的时候,这就意味着需要往商业公司去靠拢,它理想的光环可能会消失,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涂涂:是的,我此刻就在这个节点上。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件事情,想过非常多的可能性。乐府应该变成一个更健康的、更商业的、更正常的公司,那么它理想和梦想的部分怎么办?
我想过再另外做一个品牌,但最后发现这是不对的。如果另起炉灶,其实无非是把过去五年再重复一次,它还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就必须从内在来想解决方案,坦诚讲,这个解决方案现在并没有浮现。
只能说现在是在摸索阶段,短期来看可能是一种妥协的可能性。比如引入一部分制度,但这个制度不强,依然可以给出一定自由弹性的空间,但需要保证它比较低限度的系统保障。系统不仅对公司的安全极其重要,对个体的安全感也是种保障。因为当公司制度完全自由的时候,员工其实处于一个不怎么安全的状态中,而一旦员工产生焦虑,就会影响创造。所以我想找到制度的平衡点。
在产品上我会倾向于稍微往后退一点。我们到现在为止出了80本书,还有150种待编,这个数字对我们这种体量的公司是巨大的。我会收到同行非常多善意的建议:你应该少做一点,应该拿出去一点。有一些项目是处于停滞状态的,即便如此,乐府文化正在运作的选题数量还是很大。
很大程度上,乐府文化在选题上的任性,其实不是编辑部的任性,而是我个人的任性,我觉得这个应该做,就得签下来。
我现在的倾向是,目前的150个选题要再捋一遍。我们签一本书的时候都会对它有一个市场想象,有的时候能做起来,有时候做不起来,我倾向于认为做不出来肯定是我们在后期做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东西做得不对,无论是设计、定位、定价,还是对它的传播。
当然,现在的体量也不一定能缩回来,缩回来也是一种能力。
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出版人》:乐府文化一直以来做书的品位都受到许多同行的尊重,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市场狭小的切口去尝试?最开始一年做一本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涂涂: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我只会做这种东西。当然,我也可以说好听一点,说我们不做**和**这样的公司,其实是我做不了这种公司,也做不了这种产品。
乐府文化的第一本书《寂然的狂喜》是路上偶然碰到的。离开新京报书评周刊前,我去一个艺术家做的版画展览,交流中他和我提到他还想把爱尔兰的版画展览搬到中国来,他想做一个册子。我和他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来尝试一下,把它做成一本书。
所以这是一本碰出来的书,这本书能不能做成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居然做成了,这是一个意外。直到下印之前,我们合作的出版方都还反对我们把书做成那个样子。但是推完之后15000册立刻就卖掉了,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鼓舞。但是这本书其实是亏钱的,出版方与我们的结算价是一本36元,但我的成本做到了38块钱,卖一本就亏两块钱。三年之后我们有了印制的老师,他把这本书拆开了算,印制成本可以做到20块钱一本,但是最开始我们的成本是29元一本,这9块钱就是学费。
我们真正策划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故事》,作为一个第一版的书,它也是成立的,但我们设计得不太友好,竖排、高定价、精装。在这个情况下,这本书还是卖到了3万册,证明了文本的生命力。但是我们对它的定位也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我当时相信这是一本百万销量的书,我们正常卖10~20万册不成问题的,最后没实现我想象中的期待,会有一点灰溜溜的感觉,但是它还是可以支持我们公司走下去——当时我们就三个人。
《出版人》:从乐府文化过往的产品来看,“故事”是一个关键词,从品类上说,其实是文学。在文学出版如此衰败的当下,你们如何理解你们在做的生意?它的市场空间又从何而来?
涂涂:这个话题要回到根源上,我只会做这类产品,我不会做别的,这是其一。
第二个方面,很多年前我和新京报书评周刊现任的主编马培杰聊过一次天,他认为我们的书特别小众,表示了对我们的担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书其实不是小众书,我们每一本书几乎都是面向所有人,但是如果你不能细分出一个市场,不能针对某一群人,那针对所有人就是一句空谈。
我认为我们的产品针对的是所有人都可能在人生面临的一个心灵状态,所有人都可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节点看到,看到这个产品可以自然地说,“这就是我,会引起我共鸣的东西。”
这是我底层的市场逻辑。文学和艺术是和心灵相遇的东西,所以我做的就只能是故事和文学。
对一个人,我要等待他的心灵状态,对市场,我也需要等到市场到那个点。等不等得到,我是不知道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做某些东西,比如说《三十六岁人生半熟》就意味着20岁的人不会看,40岁的人不用看,它相对精准框住了人群范围,反而能够跳出来,在我们的书里,这本书是表现比较好的。所以我会努力在它的传播做一个限定性的解释,但是我的底层逻辑不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我没有能力做某一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所以在大的层面,我是只能等的,最后把自己等死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小的层面上会跳一下,从所谓的普世感里跑出来,做一些相对精准的东西。比如说做《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会知道中国的民间故事是一个缺口,做《诗人十四个》时也会知道对古典中国的现代性阐述也是一个缺口。
《出版人》:我们感觉到,乐府文化的产品一直在选择不确定性,在商业上这个其实是很奢侈的东西,整个行业从主观和客观都在丧失这种勇气,但是在不确定性中你们怎么去判断文本的价值?
涂涂: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种天才,恰好我拥有这种天才,就这么简单。比如说出了《秋园》之后,有很多类似的文本找到我,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很多文本是不对的。杨本芬是一个文学天才,只是她以前没有写,所以《秋园》不是一个老人家写的一本书,而是一个天才老了才写书。这个是根本性的东西。
另外就是在等待文本这件事情上,我很有耐心。就这么两点,我就知道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找到优秀的文本。
我可以接受它失败
《出版人》:作为一家商业公司,你们也需要从不确定性往确定性去靠拢,你们怎么解决这中间巨大的鸿沟?
涂涂:我们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是包装也好,还是传播也好,基础的动作都会做,但是真正从行业上来说,这些东西都不会指向确定性,也可以说我缺乏转化能力,如果我有转化能力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的产品就应该能实现它。
这五年里,乐府能活下来,很大程度上我会归结于偶然。当然,也有一部分必然。你的选择、你的努力会被一部分人看到、放大、尊重,并且引以为同类,你会遇到世界的善意,在你猜测不到某一个路径,它会有一定的商业转化,所以说善意让我们活下来的。
反过来我会觉得把书做成这个样子,是我能给出的善意,因为我没有钱,那我只能做这个事情。
但是善意能让你最终活下来吗?我觉得也不对,你不能仅凭善意,不然你就变成一个非盈利机构。我们终究还是商业的,虽然我们还会不停地输出善意、遇到善意,但是如何不依靠它活着,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出版人》:从乐府文化选择文本的逻辑来看,挣钱的书一定是少数,这也意味着它对那本挣钱的书要求特别高,然后去反哺其他的产品,但是现在乐府文化还没有等到这一本书,你有没有考虑过融资或者找一家大的同业企业收购掉?
涂涂: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你说的方案我确实也都聊过。我最近在做一本美国唱片公司老板的回忆录,他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许多流行音乐巨星的发现者,他完全不懂音乐,但是他对人有强烈的嗅觉。最后他在最后的生死线上就是把自己卖掉了,变成一个持股20%的小股东。变成这个样子后,他会遇到极大的系统挫折,系统让他存活下来,但是他就会错过一些新的人,要付出巨大的妥协成本。
在看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有强烈的感同身受。
我想过找一个同行业的一家大机构,它肯定能带来巨大的系统支持,也想过去融一些钱。去年在“做书”上发完那篇文章后,有朋友来找我说如果需要钱的话,可以给我一笔钱,他说我觉得你能做成,而且可以完全不干涉你。
看上去都很好,但我还是会想,这是真的吗?说这么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来了之后真的能不干涉你吗?以及多少才算够,如果给了我500万或者1000万,还没有等到头部,怎么办?
我也会想,即便是有一家大企业愿意接受乐府,产品要做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的市场想象空间其实是有的,但是与整个行业相比,它有路径困难,它太新了。
有时候因为你为了要让自己活下去想缩短这个时间,但是从客观来说,它确实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哪个作品会不会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成为经典作品。我的冲动在这里,我希望我能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而这个经典作品到底是哪一个,这是需要运气的,不能由我来确认的,我说了不算。
所以这个真的一个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现在只能说我还在思考它,也希望我们重新调整制度和架构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强化我构建系统支持的能力。
我在想,我们已经出的80本书和即将要出100种书,能不能重新盘活它们?逻辑上是存在可能的,因为有的书虽然没卖起来,但是它在市场的想象力依然在哪里,好像还是有空间的。问题是我怎么去构建,能不能做到?
我也想过有没有可能在我的书上,或者通过视频号、公众号给最一线的读者们来讲一个不那么卖惨的故事,在读者那获得支持,从而完成生死线的跨越。这个从商业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不过现在仍是基于空想,也不见得会去做。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创业狂人,夜以继日地扑在上面,也许就会做到,但是那就不是我了。虽然我认为乐府这个公司对我极其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根本性的东西,但是仍然不可能让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我不是那种人,换句话说,如果我是那种人,我们就不会做出那些东西,乐府本质上是反对这个的。
在这个层面上,我会觉得哪怕这个公司做了5年,承载了很多人的期许,尤其是同行们的期许,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它失败的,然后再往前摸一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