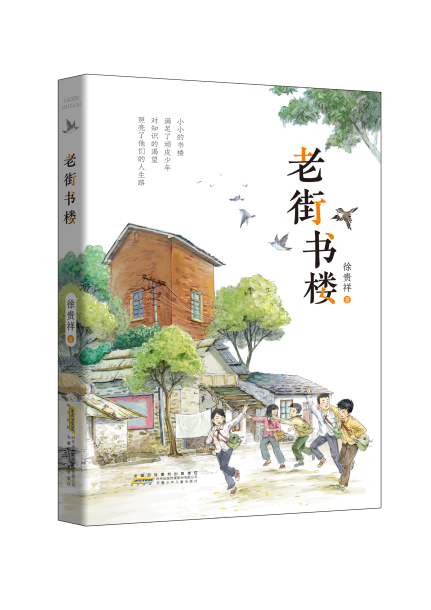我们在包装盒外印上黑色的石头和那句话“只要人类还在讲故事,我们就还是我们”。让每一位打开这套书的人,做好回到故事和童年的准备。
文|李 洁

2016年3月的一天,在蒲蒲兰做营销工作的秋兰忽然发微信给我,问我想不想换一份工作。“想。”我立刻回复。
第二天下午,在劲松附近的一个咖啡馆,我见到了涂涂,乐府文化的创始人。
开场白之后,我很快发现面前这个人实在太会讲故事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听了一下午故事。除了聊有趣的书与人,更主要的是乐府文化成立的故事:几个好朋友,有媒体人、教师、出版人、书评人,坐而论道多年后,想要亲身实践做出版。
那天谈了很多书的计划。“可以从故事开始啊。故事、歌谣、音乐、绘画,等等,一切美育的东西,更能回应和滋养人的精神。当然,这些东西也可能来自土地,来自遥远的过去和偏远的地方,来自少数人群。上海文艺出版社在90年代初有一套很棒的原典故事,来自非洲、挪威、法国、北欧、德意志、俄罗斯,还有亚洲,收录了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对了,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做了很多很多童谣和故事。这些书离开读者的视野很久了,我想做出来。”
“给孩子?”

“给孩子,也给所有的大人。人天生需要听故事,故事传递的心灵力量不可小觑。读和听大量的民间故事,让我们具有多元的文化意识,而且故事拥有大量充满想象力的隐喻,让精神世界变得宏阔。”
关于乐府这个公司名字的解释,乐府的好朋友朱桂英特意写道:乐府(LO·VE)取其本意,源自民间的歌谣、阡陌和曲,也取哥林多前书,8·1,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
我们签第一部外文版权的时候,又拟定了公司的英文名Pan Press。
乐府,会是一个用故事造就的永无岛吗?
故事来自世间生动的一切
回到《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这套故事集的推进,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毕竟除了体量大之外,老一辈编者和译者的语言习惯也需要与当代读者重新勾连。如何让读者欣然打开古老的故事,去识别文字之下的观念和心灵,编辑要先找到故事的入口。
送去录入文字之前,我打开了北欧卷,读到一个熟悉无比的故事——《灰姑娘》。但这个“灰姑娘”是来自瑞典的民间故事,与我们熟知的格林童话中的版本相比,它竟然包含了“灰姑娘后传”。我忍不住给女儿读了这个故事,她很直接地评价:“以前看到的灰姑娘是个可怜又幸运的小女孩,这个灰姑娘却像大地女神盖娅。”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常常被孩子们代入自己,那个总不被重视的、受尽委屈的、没有力量的小孩子,当有神奇魔法的帮助,就会幸运加身,摆脱困境。但是,穿上水晶鞋、与王子结婚的灰姑娘,就得到幸福了吗?瑞典的版本第一次带领我和女儿看到灰姑娘需要自己承担苦难,看到她穿过苦难后的幸福。这个“后传”如此厚重,小读者的心也如此敏锐。
瑞典版的《灰姑娘》成功为我打开了通向1000多篇“讲了100万次的故事”的大门,我相信这套故事集的丰富性将是无可比拟的。
“讲了100万次的故事”,是涂涂后来定下来的名字。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完全源于口头讲述的故事,很多已经传承了千百年,说它们被讲了100万次,一点儿也不夸张。故事被口口相传,又被寻找故事的人记录和写定——这个过程我们是如此熟悉:德国有格林兄弟;中国古有蒲松龄、现代有林兰,甚至鲁迅先生也是记录故事的人;1949年后,山东的董均伦夫妇收集整理的《聊斋汊子》更是珍贵的民间故事宝库。那些被收集的故事,有些很小很日常,有些是奇异的,有些是夸张的,但所有留下来的故事都生动有力,魅力不减。《讲了100万次的故事》也一样,没有文字的疏离感,因为它们的来处就是世间生动的一切。
人类童年故事不谋而合
三年的时光,在阅读、与译者沟通中,与各位同事的讨论争执中,这套故事集的文本面貌越来越清晰。我总会反复琢磨瑞典版的《灰姑娘》。整个套系里面,这位灰姑娘王后的故事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形,有时候她是十二只野鸭的妹妹,为了救哥哥而在众人面前沉默不语;有时候她被变成小狗,只有每个周四能去哺育孩子;有时候她甚至是扒着炉灰被众人嫌弃的灰小子,但只有他拿到了妖怪的心,娶得公主、成为国王。在《中国故事》里她也出现了。
编辑这套故事的同时,乐府文化出版了一苇重述的《中国故事》,一苇就像格林兄弟或者阿斯别约恩生一样,是一个寻找故事、记录故事和重述故事的人。通过她,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国唐代笔记故事集《酉阳杂俎》中有一篇《叶限》,比法国的灰姑娘早了八百年。故事情节几乎重合,依然是被继母虐待的女儿和金色绣鞋的魔法故事。
在古老的时代,不同地域的时空隔绝,文化差异巨大,人类却在讲同一种故事、甚至是同一个故事,心灵和情感如此相通。如果不是通过讲故事,我们很难发现人类这种共通的心理,这种不谋而合的希望和意志。
当然,不谋而合的,不仅仅是希望和意志。人类的童年故事,交织着相似的无知、聪慧、恐惧、好奇、热爱、憎恨、希望、狡黠、投机、信仰、残忍⋯⋯它们在没完没了的故事里幻化,有时让我们吃惊不已。
《讲了100万次的故事》中我反复读的第二个故事是《太阳以东,月亮以西》,这个故事几乎集齐了上面所说的故事中的一切。它让我鲜明体验到一种真实和慰藉:孤单的孩子所恐惧和担忧的都会发生,所向往和努力争取的也终会得到。
这是个相当完整和饱满的民间故事,因为它,我对整个丛书更充满信心。我把故事讲给朋友和爱人听,他们有的小时候听过,还看过台湾拍的动画片;有的觉得这就是永远会流传下去的童年睡前故事。“充满北欧风情,又好像是全世界最典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将会有1000多篇重新回到读者眼前。
乐府像打开了故事宝库的大门,中国的、世界的,从古至今,没完没了的故事在不停被讲述,人们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故事。
寻找古老故事的现代性
《讲了100万次的故事》,文本反复审读、打磨的时间之长,将我的神经绷到了极限。幸亏我们终于启动了一件开心的事情:重新为故事做插画。
“当然是孩子的插画了。”涂涂很肯定。用孩子的插画与古老的故事交织,找到现代人阅读这些故事的连接点——这成了乐府所做一系列图书的常有动作。
好朋友推荐我们找到了北京朝师附小的美术老师陈君,她带着一群三四年级的孩子埋头创作版画。
“只给我们看故事的只言片语吗?没问题。”陈老师和孩子们答应了创作。
每一卷故事,我们给出了十个左右的句子。一个学期后,孩子们交稿了。就是如今大家看到的这些拙朴又现代的版画作品了。
古老的故事的现代性正是在与这些孩子的连接里面。
孩子窥得故事的点滴,先用艺术创作想象出自己心目中的故事,当他们看到古老故事的全貌,会多一份自己的解读,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故事的阅读者、讲述者,抵抗住了那个叫做“遗忘”的东西,也会讲出自己的故事。
古老故事的现代性还在如何讲述里面。
非洲卷最典型,编译者董天琦先生在非洲工作学习多年,不但编译了大量非洲本土已经传播和写定的民间故事,更在刚果(布)作为“寻找故事的人”,现场记录整理了五十多个口传故事。这第一手的故事,由一个现代学者记录和讲述,古老的观念与现代的语言文化碰撞,所得故事就是古老又现代的。读者可以在非洲卷中看到起源故事中人类的乐观和执着里透着某种对神的“不敬畏”、某种“混不吝”的生机勃勃,也可以看到深具非洲特色、充满幽默和讽刺的动物故事,与俄罗斯的动物故事绝然不同。非洲故事和印第安故事带来的新鲜感和原始感一直并存,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块大陆的民间故事和神话过去很少进入主流阅读的视野,另一方面,在这两块地域文明发展的最初,内部发展的不均衡让人类活动呈现出非常多样的状态,所以故事格外丰富。
用贴近读者心灵的方式呈现
古老故事的现代性,是出版者需要从内向外呈现的。
乐府成立之初,就想要将这些来自大地深处的故事和歌谣,用贴近读者心灵的方式呈现。故事集是厚重的,但我们的书要稍微轻盈一些、亲切一些。所以,首先确定了它是一套干脆利落的小精装,不要外封,不要太重。
设计师晓晋是乐府多年的好朋友,曾经拒绝过我设计童书的邀请,她说:“我不了解孩子。”但是,对这套书,她没有任何犹豫。因为这套书不必迎合孩子,也不必迎合大人,它本身带着每个人对人类童年的想象和观念。
对一本书或者一套书的想象,就是乐府的产品的起点。很早之前,涂涂看到莫非老师的摄影作品,就说过,可以试一试用那些树皮的细节做这套故事的封面。后来,我们又想象用代表世界的原初的意象作为主图。直到跟晓晋反复沟通,又提出在古老的意象之外,在正封处放一句话,代表故事的开始。八句话选好之后,就全部交给晓晋了。等待期,依然是反反复复的文字修改,和一次又一次关于装帧的想象。直到有一天,晓晋告诉我,她用的那个意象,就是石头。
这套书的封面,一稿就确定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斑驳却有一种轻盈感的石头在时间流逝中横亘天地之间,石头似乎不言语,故事却从其间溢出。孩子们的版画被石头半遮,好似观念的内核需要被打开。当你打开书,版画的全貌在环衬上自然呈现。
晓晋的用色很少有饱满的时候,这一次依然不追求饱满,却与孩子们的版画氛围奇异地相合,呈现出一种饱满的效果。
我们在包装盒外印上黑色的石头和那句话“只要人类还在讲故事,我们就还是我们”。让每一位打开这套书的人,做好回到故事和童年的准备。
2019年末,我把故事的最后一个审次的稿件全部带回家,准备用两个月时间再审读一遍内文。然而,2020年春节却以极其特殊又猝不及防的方式打开了。
沉默又情绪满溢的三个月里,是这1000多个故事助我沉静下来;同时是疫情让我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才又精心校对了所有的文字和内容,重新集中读了所有的故事。
涂涂在四年前所说的关于平行的关系、独立的人的话,在这个情境中格外凸显出来。每个人都很孤独,很大的、很理想主义的话语不再能够抵挡直面自我的空虚。很多小公司和很多普通人在疫情中风雨飘摇,我们能做的只有保持和依仗那个独立的“我”,在情绪之外,坚持我的和我们的故事。
穿越过这样的经历,重新审视故事,会发现粗粝的遮蔽早已消失,古老的故事是非常坦荡的,它们或许还没有承载文学艺术的更多功能,它们昭示的内核依然会被今天的我们一眼识别出来,并且有更多不一样的解读。
这样的故事,是真正具有现代性的。■
(本文作者为乐府文化编辑)